分类导航 / Navigatio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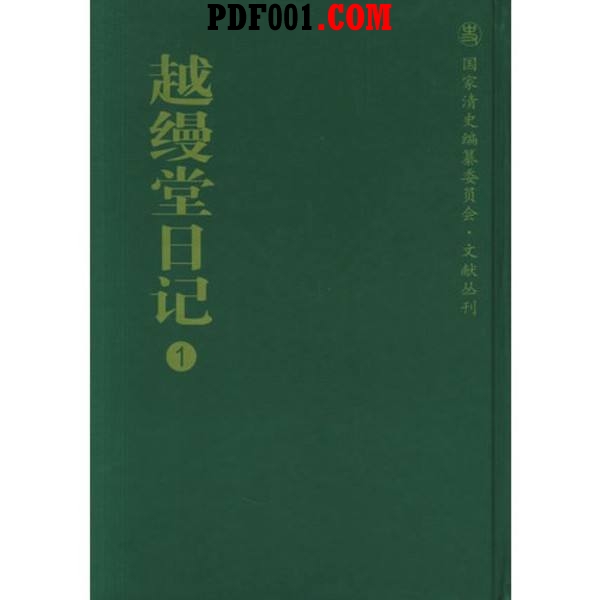 越缦堂日记 全18册 清代李慈铭著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价 格:¥ 39.80
30天售出:141 件
商品详情
注意:《越缦堂日记》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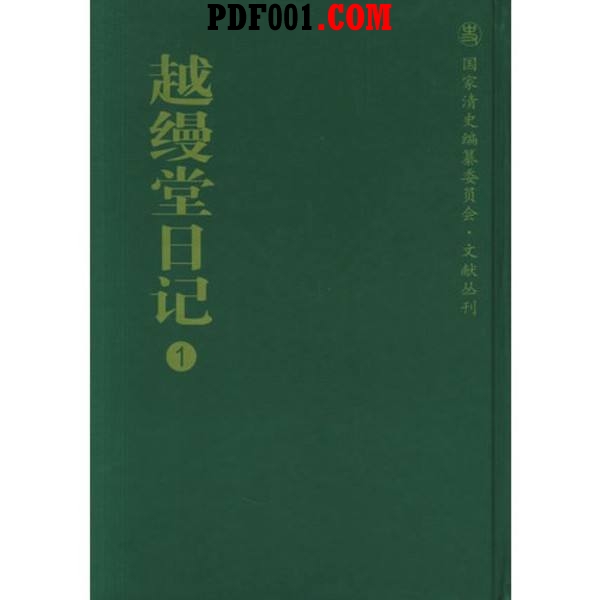 《越缦堂日记(套装共18册)》是李慈铭积四十年心力,铢积寸累而写成,日记共包括《甲寅日记》、《越缦堂日记乙集-壬集》、《孟学斋日记》、《受礼庐日记》、《祥琴室日记》、《息荼庵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荀学斋日记》、《苟学斋日记后集》九部分。洋洋数百万言,不仅记载了清咸丰到光绪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及各地风俗,足资后世学者参考,同时书中也记录了他的大量读书札记,“略如四库全书提要之例,而详赡过之”,学术价值极高。因此,该日记也可谓是李慈铭治学的大成,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其他三者为《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和《翁同龢日记》)之首。日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印出版后,曾风行海内,士林争以一睹为快,受到当时及后世学者的高度重视,鲁迅、胡适、黄裳及孙犁等著名学人都有所撰述。 作者:(清朝)李慈铭 李慈铭(1829——1894),清末著名文史学家,号莼客、越缦老人,室名越缦堂。是清末同光之际才望倾朝的学者,被后人誉为“旧文学的殿军”。其人仕途蹭蹬,困顿落拓,但其清高狂放,以致遗世有“性狷介,又口多雌黄”之讥。然其穷年孜孜,笃学不怠,于诗文、考据、小学等均有精深造诣,声名斐然。
目录 第二册(咸丰八年一月一日——咸丰十年六月十六日) 第三册(咸丰十年六月十七日——同治元年三月三十日) 《越缦堂日记》的版本及整理出版情况简介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 李慈铭(1829—1894),晚清著名文史学家,清末同光年间才望倾朝的学者。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初名模,字式候;后更名为慈铭,号莼客,所居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清道光三十年(1850)秀才,次年补廪生,屡应乡试不中。咸丰年间入京,纳赀为部郎。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补户部江南司赀郎,后累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 李慈铭一生仕途蹭蹬,困顿落拓,但又清高狂放,遇事敢于直言,以致世人有“性狷介,又口多雌黄”之评。他博学能文,兼擅诗、骈文、词曲、考据诸方面,造诣颇深,成就斐然,尤其是积40年心力所记《越缦堂日记》,集其治学之大成,与《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早在李慈铭在世时,《越缦堂日记》就被“士友多传抄之”,同治、光绪间文人圈内甚至有“生不愿做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李慈铭的日记之所以倍受学界青睐,一方面固然在于李慈铭本人的名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记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日记对清咸丰到光绪近40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名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以及北京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均有翔实记述,足资后代学者参考借鉴;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读书札记,仿《四库全书总目》之例,撰写书籍介绍及评论,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日记中还录有李慈铭本人的诗词、骈文作品,对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学创作颇具参考价值。 《越缦堂日记》的出版经过极为曲折,前后历时60余年,分三段三次进行。清光绪甲午年(1894)末,李慈铭病逝,遗留日记手稿70余册。当时,沈曾植、缪全孙等人曾极力推动将日记付梓,曾经师事李慈铭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后一盒(日记)去,卒未刻”。至民国八年(1919),在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王书衡等及学界20余人的共同捐助下,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九年(1920)影印出版了现存64册日记稿的后51册,是为李慈铭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至光绪十五年七月初十期间的日记(中间亦有短暂辍记)。1935年10月,在钱玄同的倡议下,由蔡元培主持,其余13册日记,仍由商务印书馆石印出版,名为《越缦堂日记补》(1936年),是为李慈铭咸丰四年三月十四日至同治二年三月三十日期间的日记(中间亦有短暂辍记和毁失者)。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界曾有过铅字排印《越缦堂日记》普及本的动议,但未能付诸实施。 而樊增祥带走的李慈铭暮年日记手稿数册(传说为八册,实际为九册)音信杳然,尽管各时期都有热心的出版者呼吁追寻,但始终没有下落,使学界难窥日记全璧。 据曾任《东方杂志》主编的苏继卿称:上世纪30年代曾在北平遇识樊增祥之女,获知樊氏一直珍藏李氏日记,樊去世后家人将日记转让给某书商;敌伪时期又辗转为汉奸陈群(人鹤)所获,抗战胜利时则为汤恩伯接收。因此,郑逸梅在《清娱漫笔》中预言,“所谓已被毁的部分日记或许尚在天壤间,但不悉何时始得出现”。 1988年3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署名“海波”的文章,题为《关于李越缦<郇学斋曰记>》,该文章披露:这宗珍贵的手稿已经失而复得。后重见天日的这部分手稿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学斋日记》(后甲乙丙丁戊集)共九册,记事起自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一日,迄于光绪二十年正月初一日(中间亦有辍记)。至此,李慈铭日记始以完璧面世。 《郇学斋日记》的影印出版,无疑是学界的幸事,使得李氏日记遗稿得以完整流传,其学术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完整的《越缦堂日记》共由九部分组成,分别为:《甲寅日记》、《越缦堂日记乙集——壬集》、《孟学斋日记》、《受礼庐日记》、《祥琴室日记》、《息茶庵日记》、《桃花圣解盫日记》、《郇学斋日记》和《郇学斋日记后集》。日记起于清咸丰甲寅(1854)三月十四日,迄于光绪甲午(1894)元旦,共40年。但据《越缦堂日记壬集序》记载:“予自道光丙午始作闩记,至戊申冬辍,阅五年,逮咸丰甲寅春,更为之迄今。”可见,李慈铭从1846到1848年还有近三年的日记,这些日记后人恐怕无缘得见了。 由于《越缦堂日记》的出版前后间隔70余年,又流传不广,因此时至近期,对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一些介绍性文章仍然未能揭示其全部内容。2004年4月,广陵书社重新整理影印和完整出版的《越缦堂日记》,得到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重视,并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一 李慈铭(1830~1894)从清咸丰四年(1854)开始写日记,40余年如一日。如因故中断,则预记大略,得暇详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自前月校书甚忙,至无暇写日记,皆草草札记之邸抄面纸,今日始自前月初四日后补录之”。初八日,“补录日记”。初九日,“补录前月日记讫”。十二日,“补写是月日记讫”。有的也凭追忆补日记,不免恍惚。光绪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是日,补写一月来日记,毕多仿佛,不能尽记矣”。李氏不时检点旧日记,加以修饰。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终日阅旧日记,稍稍涂改之”。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偶阅旧时日记,其中多有疵谬”。光绪二年二月初六日,“偶取庚申日记检一事,因将其中怒骂戏谑之语,尽涂去之。尔时狎比匪人,喜骋笔墨,近来偶一翻阅,通身汗下,深愧知非之晚。”李氏也颇注意对日记的保存。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装订乙丑至今日记,共十五册,分为两函,今日标写签柎,颇极精整”。他的全部日记,凡72册,分为8函,另有半册。详见《北平图书馆季刊》第6卷第5号载王重民《李越缦先生著述考》。 《越缦堂日记》的发表,几经周折。先是稿本传观,继而在期刊节登。直到民国九年,始由蔡元培等经理刻石影印其中的第2函至第7函,凡51册。旋仍由蔡等经手,补印了第1函,凡13册。以往学术界咸知《越缦堂日记》共64册,即此两次石印本的合计。至于其第八函8册,则是至近年始发现并影印。 李氏常将日记给友好阅读。如同治九年十月十五日,“作片致孙子宜,索还日记”。同治十年四月朔,“作书致周允臣,借以近年日记两册”。六月初八日,“张牧臣来拜,以日记见还”。十月二十五日,“得朱鼎甫书,借日记”。“作书复鼎甫,借以日记四册”。光绪四年十月初十日,“得伯寅侍郎书,惠银十两,言昨见日记,知其乏绝,故复分廉,甚可感也”。伯寅,潘祖荫。由此可见,在李氏生前,已有多人看到李氏的日记。 李慈铭殁后,文廷式曾见其《日记》。《闻尘偶记》云:“李莼客以就天津书院故,官御史时,于合肥不敢置一词。观其日记,是非亦多颠倒,甚矣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然莼客秉性狷狭,故终身要无大失,视舞文无行之王闿运,要远过之。”善谈掌故的徐一士,由此引出《李慈铭与王闿运》一文。据《一士类稿》言:“廷式尝摘抄慈铭日记,间加批识”云云。 辛亥革命后,李氏《日记》曾经某些期刊节录发表。王重民《李越缦先生著述考》著录的《越缦堂日抄》2卷,《古学汇刊》本,即其中之一。王氏云:“《绍兴公报》、《文艺杂志》、《中国学报》相继节刊,但仅数页或数十页,均不及《古学汇刊》为量之多。其开端十数条,为印本《日记》所无,疑录自沈悦民所藏半册内。”《中国学报》刊登李氏《日记》,颇受士林重视。《鲁迅日记》: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赴留黎厂购《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四角。报中殊无善文,但以其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艺风堂友朋书札》辑吴昌绶致缪荃孙书(六十)云:“近出《中国学报》,吾师见否?如要,可购以奉呈。”小注:“《越缦日记》不同,而亦有复见。” 缪荃孙曾托蔡元培等向李氏后人求《日记》全稿。并拟节抄刊行。上书辑元培致缪氏书云:“越缦先生日记,沈子培、樊云门二君均曾力任付梓,然二公有力时均未暇及此,今则想不复作此想矣。先生拟仿《竹汀日记钞》例,节录刊行,良可感佩。李世兄尚在故乡,容即函嘱负箧赴沪,贡之左右,果能流布人间,则先生表彰死友,嘉惠后学之盛情,感佩者岂独元培与李世兄而已哉!”据《蔡元培自述》,在李慈铭殁前一年,他在李氏京寓充西席教师。以故慈铭嗣子承侯,系蔡氏学生,即信中的“李世兄”。惟此事没有达成。《艺风堂友朋书札》又辑吴重熹致缪荃孙书(十)云:“《莼客日记》四册送去。此为孙氏存本,孙氏无人,惟余内眷在闽,坚不出手,故假抄之。得方家理董成书,甚盛事也。樊山处者,亦当于家信中姑一问讯之。”樊增祥,字云门,号樊山。亦李氏故人。由是在缪氏周围又有人得见李氏《日记》的部分抄本。同书辑录王秉恩致缪荃孙书(五)云:“《莼老日记》向闻近于刘四。今读之,学术纯正,议论平实,异乎所闻。公为刊传,甚盛事也。”但终未刊行。“刘四”,似指刘体智,刘秉章第四子。 直到民国八、九年,始由蔡元培、张元济等经手,刻石影印,遵李氏遗愿,先印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凡51册,6函。其详具见于《张元济日记》。民国八年六月三十日,“晤李璧臣,交《越缦堂日记》八册”。璧臣,慈铭侄。八月三十日,“晨访鹤庼于密采号,交出《越缦堂日记》六函,又李越缦照相一张,交剑丞保存”。鹤庼,蔡元培。夏敬观,字剑丞,时佐张氏主持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九年一月三十日,“鹤庼回信,《越缦堂日记》缘起可照改”。三月六日,“崔庼来信,言江西许季黻购《越缦堂日记》二十部”。许寿裳,字季黻。七月二十日,“约谢燕堂、翟孟举、季臣,告知《越缦堂日记》无庸修润,惟与原书不符者,稍加修饰”。以上略见该书交稿、预售、印刷诸事的经过。此书出版后,即在文化人中流通。《郑孝胥日记》:辛酉(民国十年)六月初五日,“阅《李莼客日记》”。初八日,“杨寿彤复送《越缦堂日记》来,凡六套,乃陈小石物,杨借观之,复以转借”。这6套就是第一次公之于世的第2函至第7函。 对《日记》的第1函,蔡氏遵李氏之意拟整理后印行,后听钱玄同之劝,也将原稿刻石影印,以免搁置。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云:“《越缦堂日记》,近有补印十三册,《莼客日记》至是舍樊山所藏外,悉公于世间。”此已是民国二十五年事。 二 胡适也是最早阅《越缦堂日记》的一个。《胡适的日记》:民国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看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第三册。这部书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记的重要原因。”五月四日,“下午,专补作日记。日记实在费时不少。古往今来日记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真不容易。怪不得作日记能持久的人真少。”民国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连日病中看《李慈铭日记》,更觉得此书价值之高。他的读书札记大部分是好的。他记时事也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如41页39以下,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六日阜康银号的倒闭,因叙主者胡光墉的历史,并记恭亲王奕�6�0及文煜等大臣的存款被亏倒,皆可补史传。”胡适这段对《越缦堂日记》的批识,发人深思。 按其时已是中法战争爆发的前夜。阜康号挤兑事件,正是列强入侵、内政腐败交织相摩所引起的火花。有识之士,从此可觇中国民族危机的深重。胡适未引《越缦堂日记》有关全文,兹为补录: 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设阜康钱铺忽闭。光墉者,东南大侠,与西洋诸夷交。国家所借夷银曰:“洋款”,其息甚重,皆光墉主之。左湘阴西征军饷皆倚光墉以办。凡江浙诸行省有大役,有大赈事,非嘱光墉,若弗克举者。故以小贩贱竖,官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累赏御书。营大宅于杭城中,连互数坊,皆规禁篽,参西法而为之,屡毁屡造。所畜良贱妇女以数百,多出劫夺。亦颇为小惠,置药肆,设善局,施棺衣,为饘粥。时出微利以饵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其邸店遍于南北。阜康之号,杭州、上海、宁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万计。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争寄重赀为奇赢。前日之晡,忽天津电报言南中有亏折,都人闻之,竞往取所寄者,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溃,劫攘一空。闻恭邸、文协揆等皆折阅百余万。亦有寒士得数百金托权子母为生命者同归于尽。今日闻内城钱铺曰:“四大恒”者,京师货殖之总会也,以阜康故,亦被挤危甚。此亦都市之变故矣! 查《翁同龢日记》云: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六日,“京都阜康银号,大贾也,昨夜闭门矣,其票存不可胜计,而圆通观粥捐公项六千两亦在内,奈何奈何!”两部《日记》相比,显然李优于翁,敢揭时弊。 对胡光墉破产案,清廷责令浙江巡抚刘秉章负责清理,将其财产分偿债务。以故秉章之子体智所著《异辞录》,颇追记此事内幕。兹节引与《越缦堂日记》相印证。“光墉字雪岩,杭之仁和人。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王壮愍自苏藩至浙抚,皆倚之办饷,接济大营毋匮。左文襄至浙,初闻谤言,欲加以罪。一见大加赏识,军需之事,一以任之。西征之役偶乏,则借外债,尤非光墉弗克举。迭经保案,赏头品衔翎,三代封典,俨然显宦,特旨赏布政司衔,赏黄马褂,尤为异数矣。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钱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金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国库支黜有时,常通有无,颇恃以为缓急之计。”但“未久,光墉以破产闻。先是,关外军需,咸经光墉之肆。频年外洋丝市不振,光墉虽多智,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能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于是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上海道邵小村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于是存款巨万的协办大学士文煜等纷纷出手,向刘秉章请托,索胡光墉的财产,作为抵偿。结果文煜获得了胡庆余药肆之半,这是一块肥肉。但据《异辞录》说,有一行脚僧人以500银元存于杭州胡氏开设的典肆,苦苦索求,只得到了一些妇女衣服,折价作抵。那僧人痛哭而去。由此可见,阜康号的倒闭事件,进一步暴露了当时的腐政。一事牵引全局。《越缦堂日记》所记时政甚多,如杨乃武冤狱翻案等,而胡适独举斯例,谓可补史传,足征卓识。 李慈铭毕生勤学,涉猎四部,多留批识。金梁《瓜圃丛刊叙录》内有《越缦堂书目跋》,谓尝见李氏遗书800余种于其后人处,注明手校本90余种,手批本100余种,手跋本50余种,手序记本5种,手抄补本5种,校勘记、勘误记各1种。对这些读书心得,《越缦堂日记》有所节录,然而不免瑜瑕并见,前贤多纠李氏疏误。如唐释道世,字玄恽,避太宗(李世民)讳,以字行。“《宋高僧传》始回复为道世,而著明其称字之由焉。《越缦堂日记》十六册谓‘道世’之名,不避太宗之讳,殊不可解,盖未见《宋高僧传》也。”见《陈援庵先生全集》第9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3《法苑珠林》条。又如书商以文秉撰《甲乙事案》冒顾炎武《圣安本记》印行,虽二者大有分别,但李慈铭不能辨,误以为前者是顾炎武少年所为,犹不脱明人学究气,以之写入《越缦堂日记》。见《朱希祖先生文集》(六)所辑《抄本〈甲乙事案〉跋》。以故胡适谓《日记》所录读书札记大多是好的,留有余地,这是合乎事实的。
很久没有坚持写博客了,只因这个寒假在读《越缦堂日记》。《越缦堂日记》为乡贤李慈铭所写。
免责申明:
万圣书城仅提供下载学习的平台,《越缦堂日记》PDF电子书仅用于分享知识、学习和交流!万圣书城不提供任何保证,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果对您的版权或者利益造成损害,请提供《越缦堂日记》的资质证明,我们将于3个工作日内予以删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