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导航 / Navigatio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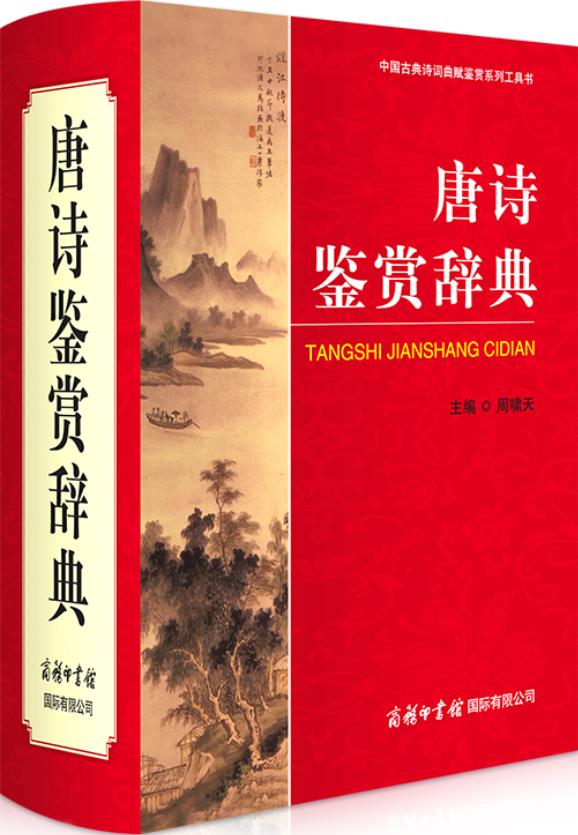 中国古典诗词曲赋鉴赏系列工具书 共8册 2012高清
价 格:¥ 25.80
30天售出:1 件
商品详情
注意:《中国古典诗词曲赋鉴赏系列工具书》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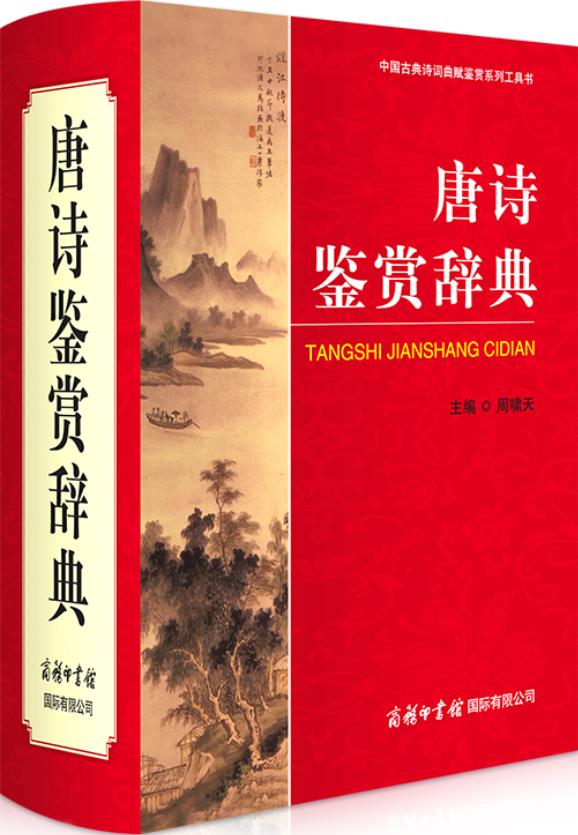 《中国古典诗词曲赋鉴赏系列工具书》PDF电子书共8册,由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
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源远流长而又得到长足发展的文学样式便是诗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这条诗的长河,向上追溯可达两大源头,即以“风骚”并称的《诗经》和《楚辞》。这两部诗集从诞生之日起,便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历代诗人,没有不受其甘泉之滋润,没有不被其光辉所照耀的。
《诗经》除有争议的《商颂》外,基本上是一部周诗。就其时代可考的作品而言,最早要算《豳风》中以周公东征为背景的几首诗,本事在公元前1114年前后;最晚的则数《陈风·株林》,诗嘲陈灵公淫夏姬事,在公元前600年左右。(按何楷《诗世本古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以为,《曹风·下泉》乃“曹人美晋荀砾纳敬王于成周而作”,时当前510年。那么,最晚的则是《下泉》了。)其时间跨度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计约五个世纪。《诗经》在先秦只称“诗”,因编集作品为三百零五篇(《毛诗》另有《南陔》等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辞”,后人以为乃“有声无辞”的“笙诗”,大约本来就是无字的歌),又称“诗三百”,至汉始尊为经。
《诗经》中可确知作者之名的诗篇(如尹吉甫《崧高》《烝民》,寺人孟子《巷伯》,许穆夫人《载驰》等),为数微乎其微。然从三百篇反映的生活内容及抒情主人公身份仍可看出,周代诗歌作者分布阶层很广,既有王公贵族之作,也有“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鲁迅《门外文谈》)。就风诗产生的地域而论,包括今之陕豫鲁晋鄂等黄河流域极广阔的幅员。它们在周代便得到奇迹般的结集,其间颇赖音乐的伟力。中国诗史中,乐府声诗占有极大优势,从汉魏乐府、唐人律绝、宋元词曲及于明清传奇戏文,成为-一大传统。而早在春秋时代,便已有“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的记载。一部《诗经》,完全有资格称为周声诗或前乐府。秦汉典籍追记的采诗、献诗制度,及近人推测周太师当为《诗经》实际编纂人(朱自清),虽无确据,却也不失为合理之推论。孔子在整理校订诗乐和推动《诗经》的传播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功绩,但“删诗”之说大抵为无据之传闻。
《中国古典诗词曲赋鉴赏系列工具书》书目:
历代辞赋鉴赏辞典
明清散曲鉴赏辞典
诗经楚辞鉴赏辞典
宋词鉴赏辞典
唐诗鉴赏辞典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鉴赏辞典
元明清诗歌鉴赏辞典
元曲鉴赏辞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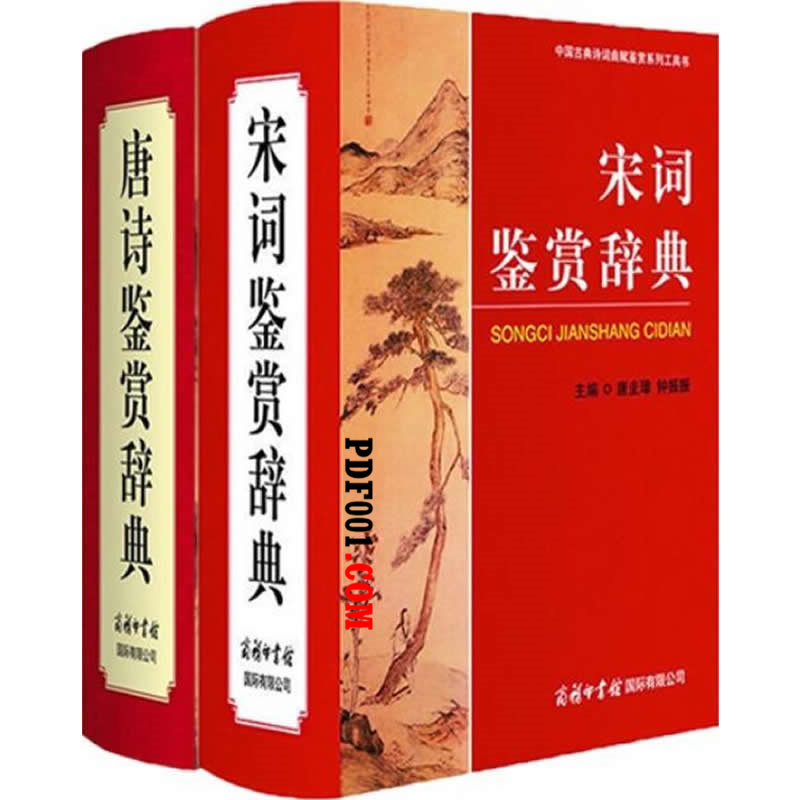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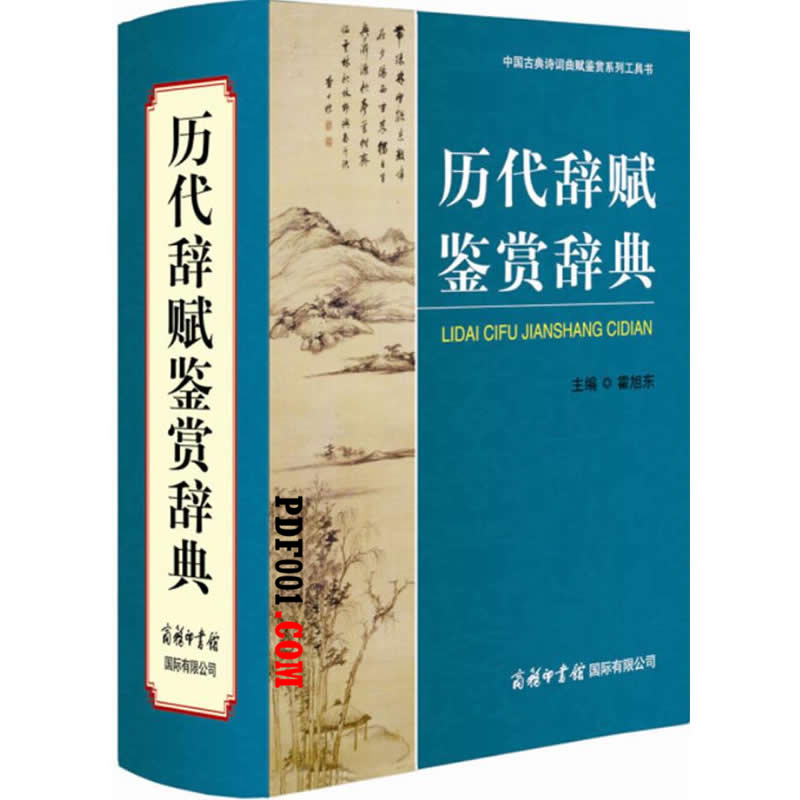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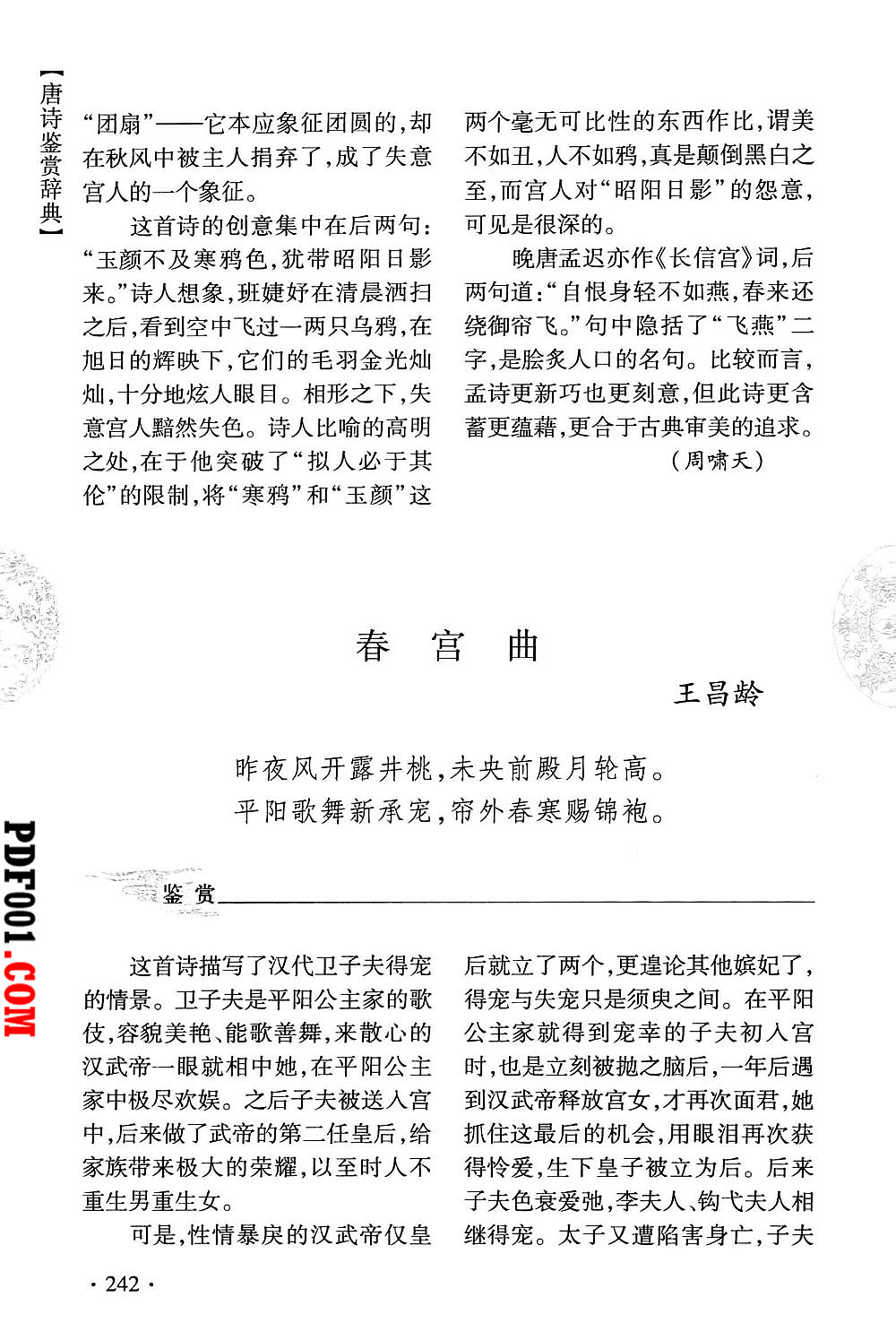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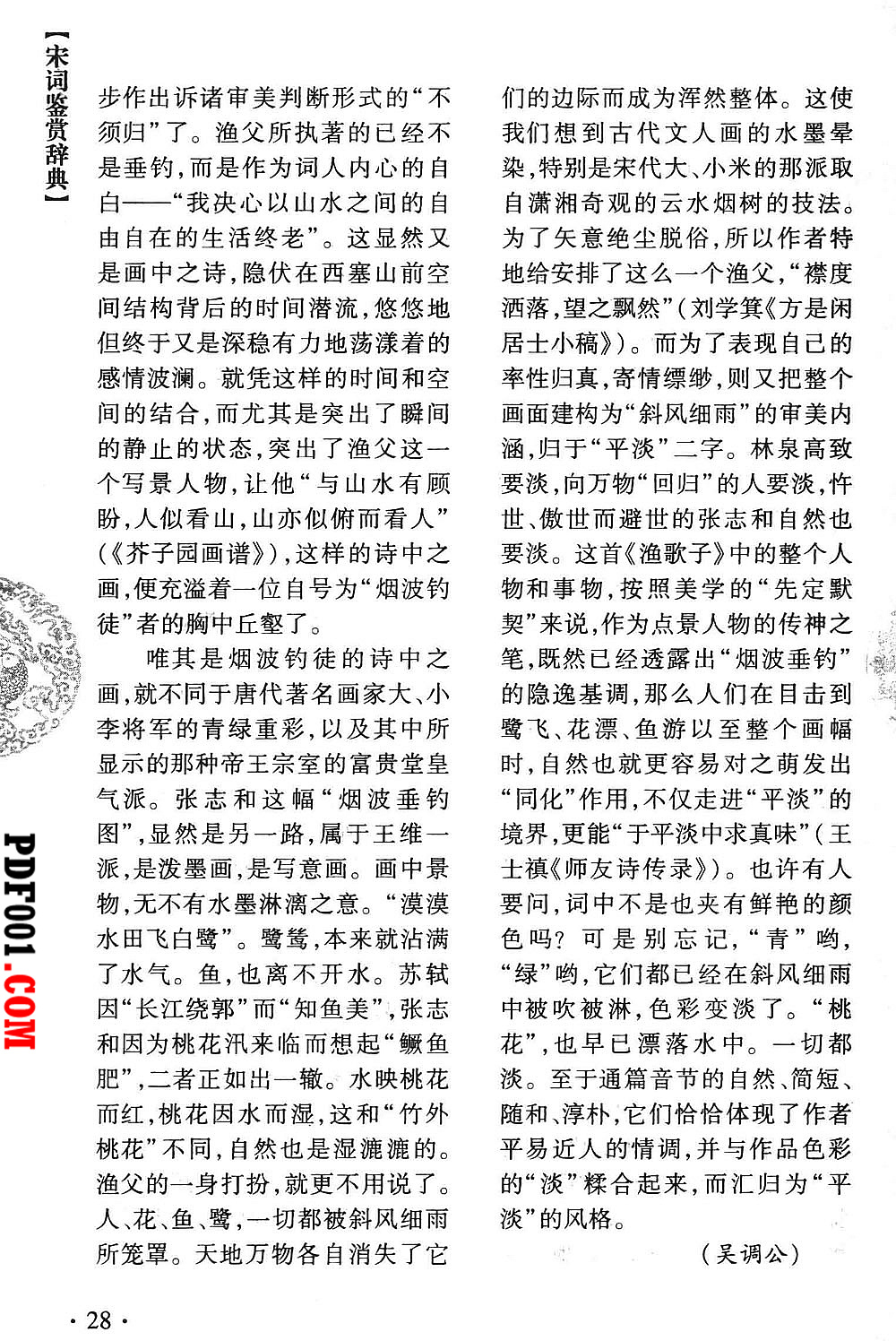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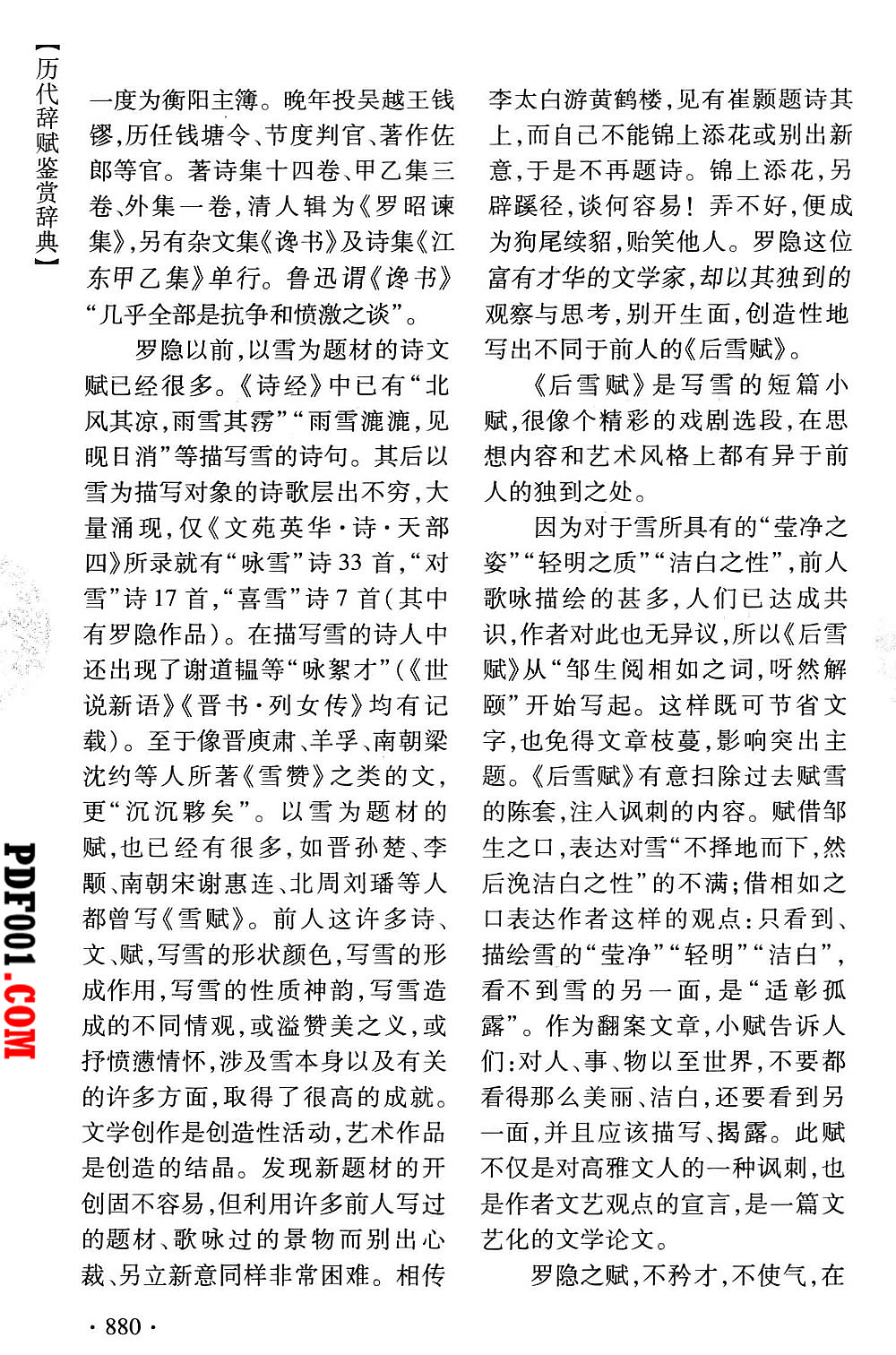 《中国古典诗词曲赋鉴赏系列工具书》出版说明:
辞赋是我国古代很有民族特色的文体。从其发展来看,“辞”和“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简言之,“赋”可包括“辞”,“辞”却不包括“赋”。这需要做较多的说明,我想先从这两个词作为文体的来由说起。
“辞”的本义,据许慎《说文解字》是“讼也”。争讼必有言语乃至文书,故“辞”又有言辞、文辞之义,也通作“词”,《易传》上所说的“修辞立其诚”,即兼二者言之。从现存先秦古籍来看,当时未有称韵语为“辞”的。至汉代,才有人称屈原、宋玉等所作韵语为“楚辞”或“楚词”。《汉书·朱买臣传》“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即其例。及至刘向、王逸相继编集屈原之作,并附以他们所认定的后人悼屈、拟屈之作,称为《楚辞》,“辞”作为文体的名称就定下来了。然汉人亦称屈原之作为“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屈原“乃作《怀沙》之赋”,又称宋玉、唐勒等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即其例。同篇又称贾生“为赋以吊屈原”,其赋的体式也与屈原《离骚》《九章》等相同。可见汉人认为“楚辞”即是“赋”。故“辞赋”亦连称,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会景帝不好辞赋”,即其例。
为什么又称屈、宋之作为“赋”呢?这首先关系到对“赋”这个词的理解,且牵涉到《诗》的六义之一的“赋”,因而弄得复杂起来。班固虽说过:“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但从后文可知,其意是指赋为“雅颂之流亚”。即主要说的是内容上的继承性,而非形式上的继承性。他的《两都赋》后系以颂诗,在形式上也是学周代颂诗,但它不是该赋的主要部分。可见汉人尚未把作为文体的赋同“比、赋、兴”之“赋”联系起来。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盖始于齐梁时的刘勰。他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他释赋为铺,本于东汉郑玄《周礼》注。“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两语,如用来概括汉大赋的特点,似颇恰切。但具有这种特点的又何止汉赋,后世许多诗文亦如此,故仍涉于泛。特别是他把文体之“赋”与六义之“赋”联系起来,尤为窒碍难通。因为他所本的郑注,对六义之“赋”原是这样解释的:“赋者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也就是把赋及比、兴都当作创作的表现方法看。如把这种理解用来概括文体之“赋”的特征,则不但与多用比兴的屈赋不合,也与他本人所说的“比体云构”(《文心雕龙·比兴》)的汉以来的赋不合。故刘勰对文体之赋所作的诠释,虽然影响很大,实际上是不可取的。(今人张震泽释六义之“赋”为诵诗言志,则与文体之“赋”有相通处,见后。)按赋的本义为“敛”(见《说文》),《左传》所谓“赋车千乘”、“悉率敝赋”,《尚书·禹贡》所谓“厥赋惟上上错”等即其义。古时作赋必铺陈之,铺、赋二字音义近,故赋可训铺。作诗言志固可说是铺陈,诵诗言志也是铺陈,故赋又可训为诵,即朗诵。《国语·周语》云:“公卿献诗,师箴,腴赋。”《左传》隐公元年记郑庄公赋“大隧”以及其他卿大夫在聘问时的赋诗,都是朗诵的意思。《诗·定之方中》毛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即是对“赋”的这个含义的精确的概括。但《左传》《国语》乃至毛传所说的“赋”,都还是动词,由动词变名词而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大概始于战国晚期。现传《荀子》有赋篇,近人或疑为后人所加,姑置不论;然《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已有:“且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皆播吾之迹,华山之博也。”《战国策·楚策四》亦载:荀卿“因为赋曰”,其赋即《赋篇》中的“佹诗”之一部分,则当时赋已作为“不歌而诵”的文体之称是可以确定的。屈、宋之作在当时是否都可歌,已难确定。《九歌》应是可歌的。但到汉代,至少《离骚》《九章》《九辩》等已是不歌而诵了。这当是汉人称之为“赋”的由来。“楚辞”以《离骚》为代表,故又称为“骚”,东汉梁竦有《悼骚赋》,可能时已有用“骚”来代表屈赋之说了。
“楚辞”既可称为赋,则辞赋自属一体。即使按照后人的习惯,只将带有“兮”字句式者称为“辞”或“骚”,也应说“辞”或“骚”为“赋”之一体。但后世却有人把它们分别开来。齐、梁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既列《辨骚》篇,又列《诠赋》篇,似已稍露端倪。然《辨骚》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实与《原道》《征圣》《宗经》《正纬》等篇一道均为纲领性的论述,与《诠赋》属于分体论有别,不能理解为将“骚”、“赋”别为二体。正式把骚、辞从赋中析出另列,始于梁萧统的《昭明文选》。此书既首列“赋”类,后面又有“骚”类、“辞”类。但他在“辞”中所选的刘彻的《秋风辞》与“骚”中所选屈、宋之作在体式上无别,另一篇陶潜的《归去来兮辞》亦只是“骚”的变体;而他选入赋类的作品如王粲《登楼赋》、司马相如《长门赋》之类,在体式上亦与“骚”、“辞”没有区别。故萧统的分类可谓自相矛盾,进退失据。至清代,程廷祚作《骚赋论》,试图按内容和艺术风格来区别骚与赋,同样也陷入矛盾。但是,以“不歌而诵”为共性的赋,如果按照比较严密的文体分类的原则去考察,其内部确有不同的分支。这些分支之间虽然有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情况,但从源到流都有某种区别。前人试图加以分析,是必要的,问题是应如何分才比较合理。我认为,划分骚的分支,应以表现形式的差别为主,同时要结合它们的源流正变来考察。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上我本人对辞赋发展史的一些认识,我认为,赋这种文体的涵盖面虽较广,变化也较多,但约而言之,主要有下列的三个分支或三种分体:
一、是以楚辞中屈原《离骚》《九章》、宋玉《九辩》为代表的一种。从结构形式和表现方法来看,它们都是一种抒情诗体,只是或两句中上句末带“兮”字,或句中带“兮”字,与某些不带“兮”字的诗有所不同。故近人也把它们称为诗。古人则或称为“骚”,或称为“辞”,或称为“骚赋”。这种赋,近人公认它是从楚国民歌发展而来的。
二、是以相传为屈原所作的《卜居》《渔父》为代表的一种。传为宋玉所作的《风赋》《高唐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则是其发展。还有荀卿《赋篇》中的《礼》《知》《云》《蚕》《针》等五赋,就其有问答而言也可归入这一类,但属于变体,且后世鲜有仿效者。(《赋篇》中后面的“佹诗”则应属下面所说的一类)这种赋基本上是一种有韵的文,其直接源头是战国纵横家的说辞和诸子中的问答体,只是它的描写部分更趋向文艺化,又有韵,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后来的汉大赋即由此脱胎。东汉以后产生的骈赋(一种俳赋)和唐以后形成的律赋,虽一般不再用问答体,内容和表现方法也更加抒情化和诗化,但就其基本体式还是有韵之文来说,仍是它的苗裔。唐宋以后兴起的新文赋更是它的嫡传。所以我认为这些应统称之曰文赋。
三、是以四言韵语为基本格式的一种。屈原的《天问》是其先导,后来有《汉书》所载贾谊的《鹅鸟赋》、扬雄的《酒赋》、柳宗元的《牛赋》等。这类赋是四言诗的变体,也可以说就是诗。作者不标名为诗而标名为赋,当是因为“赋”不仅为诵的异名,也含有铺陈之义,故把某些尚铺陈且略带文的辞气者称为“赋”。但这种赋体和四言诗的区别毕竟太少,因而后来继作者不多。南北朝时期还有以五言诗句或以七言诗句为主来创作赋的,但仿效者更少,其原因亦同。这三种赋,如果用今天的文体分类标准来看,也可以说只有两大类:一、三两种为一类,是与诗相近的,只是或不歌而诵,或偏重铺陈。汉以后,大量的诗也是不歌的,还有少数也尚铺陈,于是这类赋同诗的区别就更模糊了。特别是那些体制短小的赋就更难与诗区分,倘要寻其差异,那就是:骚或辞在语言结构形式上与五七言诗及词曲有区别,四言诗体赋则多带一点文的格调,与四言诗微有不同。但这也只是就一般情况说的,并非准确的尺度。李白的诗中就有不少是用骚体的句法写的,诗人未称之日赋日骚,后人也不认为它们是赋是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只好听从作者的意志和采取约定俗成的态度了。第二种为一类,它是近于文的。然亦有不同程度的诗化,其中的骈赋和某些律赋诗化的程度更高。像本书所选的张衡的《归田赋》(骈赋),黄滔的《馆娃宫赋》(律赋)等,我们就说它们是诗,也是可以的。
赋既然同诗和文都有牵连,因而它同那些与诗的性质相近和某些有韵或讲究声律的文之间也有难以截然割断的关系。例如扬雄的《酒赋》就又名《酒箴》,这就说明赋与箴铭类有相通之处;王褒的《洞箫赋》、潘岳的《藉田赋》也叫《洞箫颂》《藉田颂》,这又是赋、颂不分了。还有一些韵文,例如枚乘的《七发》,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韩愈的《进学解》,乃至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鲁褒的《钱神论》、陆机的《吊魏武帝文》、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等,前人或专立“七”体、“问答体”,或按作者的标题,将它归人“传”、“论”、“吊祭”、“檄移”等体。但从体式的基本特点来看,它们都与赋无别,前人对其中有的作品也径称为赋,如《七发》及所谓“七”体,前人的许多选本就列入赋一类,《说文》氐部引扬雄《解嘲》“响若砥馈”,亦径称为“扬雄赋”。因此,我认为,这些都应称为赋体文,或径称为赋。此外,汉晋以来逐渐形成的骈文(包括“连珠”体),与赋的关系也极密切,但它不押韵,就不好算作赋了。
总之,我们要给“赋”确定一个绝对的义界很难,只能大体上有个标准:首先,它必须是“不歌而诵”的韵文。但又不能把所有的“不歌而诵”的韵文都叫做赋,还要把其他已约定俗成的“不歌”的韵文体裁排除,如乐府歌诗以外五、七言诗以及箴、铭、赞、颂等,从总体上说都应与赋划境。除标名为辞赋者外,归入赋类的只应是那别无恰当体裁名称的韵文(例如所谓“七”,实不能作为一种体裁的名称),或虽标名为另一体,然不如称为赋更合适的韵文(例如《钱神论》《大人先生传》等)。这就是说,我们在确定什么是赋的时侯,不能单纯地按照一种定义去衍绎,还要以大量的已定型的赋为标准对与之有关的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不但要注意它的源,也要注意它的流。仍以前面讲到的辞和赋的关系为例,如仅以屈原的《离骚》《九章》一类作品为据,则辞或骚与赋似可分。.但汉人既已称它们为赋,后人所作与之体式全同者,也多称为骚,且后来还有骚体中夹文赋句法、文骚中杂骚体句以及句法类骚而略去“兮”字等变体出现。这样,我们就不能把“辞”从“赋”中分离出去,而只能认为它是赋的一体,否则就会造成大混乱。以四言为主的诗体赋亦然。我们若将其中更近于诗者摒于赋之中,或将某些尚铺陈且带文的辞气的诗归于赋,道理上固无不可,但同样会招来一些麻烦。在大致确定辞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裁之后,我想概括地谈一谈它的发展情况。
上面已经辨明,辞和赋是不可截然分割的。因此,楚辞自然是最早的赋,屈原也是最早的辞赋作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是“兴楚而盛汉”,即是本着这个观点。但这里也有个问题,就是盛于汉的文赋却不是骚体(尽管汉代有为数不少的骚体赋),那么,文赋是否也兴于楚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是:(1)汉刘向、王逸编的《楚辞》中有《卜居》《渔父》两篇,它们是否为屈原所作固难肯定,但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已引用《渔父》之文。从内容来看,这两篇即使非屈原所作,也非深知屈原者莫能为,因而我们至少可以说是秦以前的楚人之作,而这两篇正是汉以后文赋之祖。
(2)现传文赋尚有宋玉的《风赋》《高唐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这几篇赋,近人或疑其为伪作,但证据不足(参阅拙著《赋史》)。不过,《文选》中所收的这几篇,经过后人的润色是可能的。东晋习凿齿所著《襄阳记》中引宋玉《高唐对》即是《文选》所收的《高唐神女赋》,二者在文字上就有一些差别。但这种情况是先秦古籍流传中常有的事,不但不能据此否定宋玉的创作权,反而可以证明后人仅据其中个别词句定为伪作未免有欠郑重(当然,这并非说此事已不可争论)。(3)荀卿虽是赵人,但晚年居楚。其著书,从《史记·荀卿列传》的叙述来看,盖在晚年,他的《赋篇》当亦应作于楚。
楚辞不仅是辞赋的源头,也是辞赋的一个光辉的峰顶,对此,前人早有定评。成问题的是刘勰所谓“盛于汉”的汉赋,前人几乎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大致地说,在唐以前,汉赋及其作家在文人中是享有盛誉的。骈文家固如此,就是提倡“文从字顺各识职”的古文家韩愈,也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司马相如、扬雄都是大辞赋家。宋代的苏轼开始提出异议。他讥诮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其浅易之说”,虽主要是针对扬雄的《太玄》《法言》而言,但谓其“终身雕篆”(均见《答谢民师推官书》)则显系包括辞赋而言了。至明代艾南英则直讥汉赋不过是“排比类书”。(《王子翠观生草序》)不过,持这种看法的人在历史上是少数,许多人仍对汉赋给予高度评价。清焦循在谈到“文章一代有一代之胜”时,就将汉赋与唐诗、宋词等并提(见《易馀龠录》)。直至近代,王国维还因袭焦循的观点(见《宋元戏曲考》),章太炎也颇推崇汉赋(见《国故论衡·辨诗》)。只是到了现代,汉赋才在长时期内受到空前的贬斥,被一些文学史研究者加以“宫廷文学”和“堆砌词藻”、“呆板”、“幼稚”等等评判。但至近十年,情况又有转变,一些评论者力图从汉大赋所反映出的汉帝国的声威以及汉人的宏伟的气魄和“以大为美”的审美意识等方面对它进行肯定。我认为,在研究汉赋的价值及其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时,首先要以现存汉赋的总和为依据,而不能从一部分汉大赋出发。从现存汉赋的全体来看,它并不完全是“宫廷文学”,而有一部分是所谓“贤人失志之赋”。本书提出来加以赏析的汉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鹅鸟赋》、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逐贫赋》《解嘲》、班彪的《北征赋》…以及赵壹的《刺世嫉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即其代表。这些赋对社会问题反映的广泛和深刻是决不下于汉乐府的。其次是对“宫廷文学”也不能概加抹杀。《七发》是写给楚太子之类的人看的,可谓“宫廷文学”,但其中对宫廷腐朽生活的针砭,恐怕至今还值得深思。《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更堪称典型的“宫廷文学”。且不说《子虚赋》《上林赋》中确实反映了一种阔大的境界和磅礴的气概,有助于我们认识两汉极盛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仅就这三篇赋中所描绘的帝王苑囿的广大、游猎的豪侈和失意宫妃的忧郁来说,也是后人认识封建社会的不可缺少的形象的教材。人们往往计较于这些作品究竟是意在讽谏还是意在歌颂。我认为,即使颂多于讽,这些作品所显示的境界也是有其重要历史价值的。 免责申明:
万圣书城仅提供下载学习的平台,《中国古典诗词曲赋鉴赏系列工具书》PDF电子书仅用于分享知识、学习和交流!万圣书城不提供任何保证,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果对您的版权或者利益造成损害,请提供《中国古典诗词曲赋鉴赏系列工具书》的资质证明,我们将于3个工作日内予以删除。
|

